走向世界的“东方戏剧”

话剧《司马迁》海报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供图

话剧《司马迁》海报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供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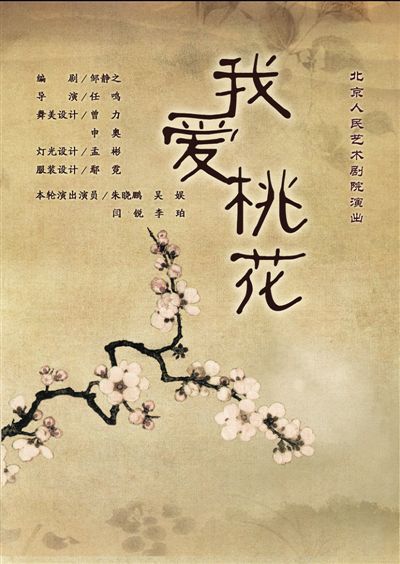
话剧《我爱桃花》海报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供图
“诗化的语言,流动的舞台,传奇的戏梦人生。”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纪念演出季剧目《阮玲玉》迎来本轮首演。故事落幕、场灯亮起,观众以长久的掌声致敬演员,也致敬导演之一、猝然离世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。
首都剧场三层办公区人来人往。坐在安静的人艺图书馆里,隐隐听到隔壁办公室热烈的讨论声——所有人艺人都在为院庆纪念活动倾尽全力。千头万绪的筹备间隙,任鸣将他对“东方戏剧”的实践、对海外演出的回忆,以及对以话剧沟通中外交流的思考,向我娓娓道来。
探索“东方戏剧”美学精神
话剧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,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存在世界化与本土化的讨论。上世纪30年代,戏剧理论家张庚提出“话剧民族化”,成为中国话剧人的普遍追求。北京人艺奠基人焦菊隐执导的《蔡文姬》中,台词步法、服装舞美均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汲取养分。任鸣这一代话剧人则从继承走向发展创新,“我们考虑的是,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前进一步、拓宽一些,通过不断的舞台实践,在话剧艺术领域内探索‘东方戏剧’的美学精神。”
这是近10多年来,任鸣思考、研究、实践最多的课题。执导一系列历史剧的过程中,他越来越多地采用一种东方视角——“不仅局限于中国戏曲的传统审美,还包括日本能剧的空寂幽玄、俳句的精炼优美、浮世绘的夸张绚丽、印度诗剧的生动神秘……”反复打磨、雕琢之下,属于东方文化的审美模式和表达方式,逐渐融入舞台的各个角落。
“这样的表达开拓我们的视野,拓展我们的创作思维。”任鸣一方面继承北京人艺历史剧的诗化风格,让观众感受到浑厚的中华文化底蕴,同时采用更新、更大胆的舞台调度和构图,积极追求视听语言的现代感,将东方美学精神与西方舞台形式融为一体。
《司马迁》的艺术风格就体现出这样的探索:舞台既具备雄浑的汉代气象,又跳出传统历史剧铺锦列绣、镂金错彩的模式。作为背景的深色汉画像随剧情发展转动,结尾时全部翻转成具有金属质感的巨大镜面,寓意“以史为镜”。舞台正中的斜面幕布透射出现代感,变化多样的灯光打造出虚实结合的意境,让司马迁与屈原的“隔空对话”更具艺术真实性。
在任鸣看来,用整个东方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滋养中国当代话剧,催生出能与西方戏剧文化平等对话的“东方戏剧”,是从业者应有的探索,“这是广泛吸收传统东方文化精髓、融合东方美学与哲学思想、同时又与舞台表达的现代精神相和谐的审美风格。这是一座引人攀登的艺术高峰。”
以“共情”激发“共鸣”
2014年,《我们的荆轲》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演出,这也是该剧的海外首演。任鸣曾回忆起那次演出,“我坐在剧院二楼,直到开场前心里还在打着鼓。”但大幕拉开后,观众的热情出乎意料,“台上是我们的演员穿着古装用中文演出,台下是1000多名戴着同声传译耳机的俄罗斯观众。他们跟着剧情笑啊,鼓掌啊,跺脚啊,谢幕时全场起立欢呼,散场了都不愿意离开……‘我们的荆轲’,也可以是世界的。”
与许多艺术门类相比,话剧的对外交流具有情感沟通更直接、思想表达更深刻的优势,与此同时,创作者必须面对传播过程中的“文化折扣”。对于人们常说的“越是民族的,就越是世界的”,任鸣有自己的看法:“民族”和“世界”共通的基础,是作品需要同时具备广泛的普遍性和深刻的人类性。他并不讳言,向海外剧院推荐剧目时,对方往往更偏爱能够呈现传统东方之美的历史剧,“我们需要做的,是带给国外观众崭新审美体验的同时,避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奇观化展示。以‘共情’激发‘共鸣’,就能把话剧演进国外观众的心里。”
创排《我们的荆轲》时,任鸣已有“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看懂这部戏”的自觉。莫言的剧本彻底颠覆了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侠士,在此基础上,任鸣将荆轲塑造为一个肩负重任又迷惘于自身价值的人,一个被功利心蚕食着理想却最终悲壮赴死、成就英名的人。这令“外国观众即便不了解荆轲,也能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找到对应的艺术形象”。
有位芬兰戏剧研究者专程前往圣彼得堡观看《我们的荆轲》,剧终后激动地拦住北京人艺工作人员,因为在剧中看到了“哈姆雷特式的两难境地”。法国《普罗旺斯日报》则这样评价该剧在马赛的演出:“这是可以超越地缘距离与文化差异的经典作品。它把故事的核心角色带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,这个普通人与你我相同,内在充满符合人性的冲突、矛盾和情感。”
让中国话剧“扬帆远航”
北京人艺亲历了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,更是中国话剧“走出去”的积极参与者。近年来,亮相海外舞台的不仅有《茶馆》《雷雨》这样的经典大作,也有《我们的荆轲》《司马迁》等集中呈现东方审美意趣的作品。而在艺术创作之外,如何帮助浸润东方风、民族味的话剧“扬帆远航”,是人艺人不断思考的问题。
话剧首先是“话”的艺术,这是任鸣常说的一句话。在海外演出时,台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演出效果,但过长的外文字幕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,影响观剧体验。考虑到这一点,《我们的荆轲》首次亮相俄罗斯时,北京人艺邀请翻译过莫言小说、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俄罗斯汉学家马义德担任同声传译。
任鸣鼓励年轻的汉学家大胆意译,尽可能将剧本中的市井俚语,以及双关、借代等字面背后的隐含意思传递给观众。“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。观众的反馈——不管是安静、大笑、耸肩、皱眉——几乎和演员台词同步。”其后,北京人艺将这一经验运用到赴海外巡演的其他剧目中,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2005年,《茶馆》出访美国,同时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大型展览。此后,“随戏带展,借戏发挥”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。在白俄罗斯,《我们的荆轲》专题展以浓郁的战国历史氛围吸引大批热情观众。在俄罗斯举行的第九届奥林匹克戏剧节《司马迁》主创对谈会上,只有50个座位的会场被百余人挤得水泄不通……展览、对谈、剧本推介会等活动迅速拉近外国观众和作品之间的距离,也为推广中国话剧、中国文化打开另一扇窗。
近年来,依托“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”这一平台,北京人艺与法国马赛拉克里耶剧院、俄罗斯圣彼得堡亚历山德琳娜剧院、喀山卡查洛夫模范大剧院等世界知名院团建立了剧目互访演出机制。来自不同国家的从业者在对话中激荡出思想的火花,并促成《知己》《我爱桃花》《我们的荆轲》《李白》《司马迁》等剧目赴俄罗斯、罗马尼亚、法国演出。得益于不断拓宽的对外交流渠道,塞尔维亚、匈牙利等国家戏剧团体纷纷向北京人艺发来合作邀请。
“北京人艺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,但它绝对不是固守陈规的‘古玩店’。它是守正创新的人民艺术剧院,更是面向世界的戏剧交流平台。”站在建院70周年的时间节点,任鸣珍而重之地留下了这样的寄语。采访结束后,他又立即回到紧张的院庆筹备中去,为他挚爱一生的剧院服务、为戏迷的节日服务……
任鸣一生执导了90多部作品,《我爱桃花》《知己》《我们的荆轲》《司马迁》等一系列探索“东方戏剧”美学精神的话剧作品走向世界,成为北京人艺探索中国话剧艺术对外沟通的优秀案例。
告别猝不及防,这位“最大的爱好就是排戏”的导演未能实现他排满100部作品的愿望。但艺术家不会真正离开舞台,因为“戏在,就会说话”。

